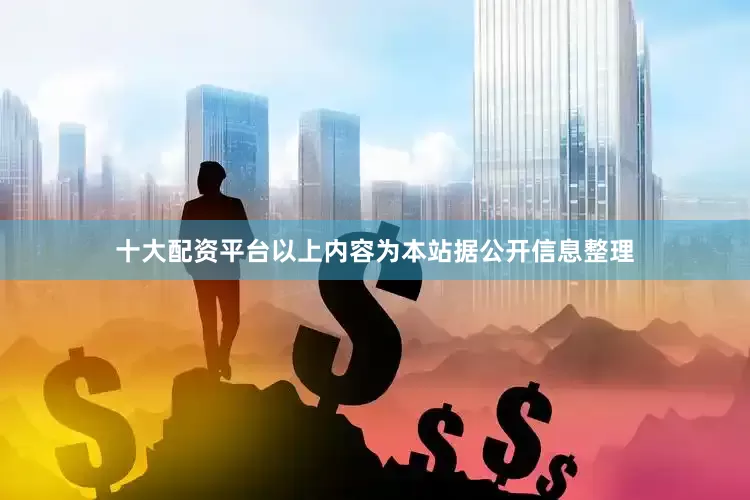叶永烈回忆:我是如何采访到陈伯达的

毛、林、周、陶、陈
陈伯达,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担任过毛泽东的政秘工作,亦为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键成员。常有人好奇,我究竟是如何成功采访到陈伯达的?
首先,尽管陈伯达已服刑完毕,然而他的住所旁便驻有公安人员。陈伯达毕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,曾位居我国第四把交椅,仅次于毛泽东、林彪和周恩来,因此他的安全与免受外界干扰显得尤为重要。正因如此,即便北京云集了众多记者与作家,却无人能踏入他的宅邸。
据公安部消息,陈伯达于1988年10月17日完成了他的刑期——自1970年10月18日起,他度过了长达十八年的有期徒刑。在刑期届满的那一天,公安部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内为陈伯达举办了刑满仪式。当时,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治疗。不久后的十几天,我便从上海匆匆赶至北京,开始了对陈伯达的采访工作。
我之所以能从上海迅速得知陈伯达的近况,并及时赶往采访,这显然得益于我与公安部长期建立的良好关系。在采访马思聪的过程中,那份标注为“〇〇二号案件”的档案,上午尚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,而下午便已转至我手中。

最大困难是陈伯达。
陈伯达,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素来鲜少接受媒体访谈。尤其在他历经多年监禁之后,他渴望的是一个宁静的晚年。加之,我的采访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他极不愿重提的那段历史。正因如此,当我告知他我的采访计划时,他毫不犹豫地表示:
“公安部方面需对我进行提审,身为罪犯,我不得不对他们的问题予以回应。然而,面对叶永烈的采访请求,我可以选择置之不理!”
此外,他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挑战:身为福建籍人士,他的普通话水平相当生疏,以至于普通人在交流时往往难以辨识其话语。
在上海逗留期间,我便预见到此次采访的艰巨性。为此,我提前搜集了陈伯达专案的相关资料,深入研读了他的众多著作,并精心编排了他的生平年谱。完成这些详尽的预备工作后,我特地前往北京。
我并未采取“直取”陈伯达的策略,而是先行展开了“外围战”。在北京期间,我深入访谈了陈伯达的历任秘书,以及他的老同事、子女、警卫员等。在积累了充分的资料与信心之后,我决定与陈伯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。
在参与“外围战”的过程中,陈伯达意外得知了我的情况。他心想,像他这样的身份,何必再撰写“传记”呢?他感慨道:“过去的往事不宜追忆,还是就此作罢吧,我如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?”

陈伯达、林彪城楼着戎装
即便我的老友已将他的话语转述于我,我仍旧坚持与他面对面交流。我深信,我仍有机会说服他接受采访。我并非那些热衷于追寻奇闻逸事的普通小报记者,我所从事的,是将对“文革”历史的采访视作一项严谨的学术研究。陈伯达,作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关键人物,对于他的访谈,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对历史老人脑海中所存珍贵史料的抢救与保存。
我初衷并非专意于为陈伯达撰写传记,实则旨在通过剖析这位非凡人物的人生轨迹,映照出中国当代史上那场深重的灾难。借此古鉴今,汲取历史经验,以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。正因如此,我曾表示,我所拟撰写的《陈伯达传》,已有十年后出版的打算。然而,鉴于陈伯达已是生命垂危,对他的采访工作已变得尤为紧迫。
经过一番“外围战”的历练,我信心满满,于是决意采访陈伯达。我深知,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,因此做了周密的准备。即便是在称呼上,我也经过深思熟虑;称呼“伯达同志”似乎不够得体;直接呼其名“陈伯达”,毕竟他在年龄上比我长了一辈;而称“陈先生”或“陈老师”,似乎也略显生疏……经过反复考量,我认为“陈老”最为适宜,一来他确实年迈,二来这是国人对长辈的尊称,既显得亲切,又蕴含着敬意。
在我看来,陈伯达肩负着双重角色:他既是历史的罪人,在我撰写关于“文革”的篇章时,我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他;同时,他亦是历史的亲历者,成为我采访的对象,我理应给予他应有的尊重。

陈伯达告知,其刑期已满,现居于北京一栋偏僻的楼顶公寓。该层楼仅有两户人家,另一户则是公安人员的住所。他与儿子、儿媳以及孙子同住一室。
因已有前约,即便陈宅门扉紧闭,陈晓农之子亦深知我至,遂为我开启。陈伯达历经三段婚姻,育有三子一女。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之际,尽管其三位前妻诸有仁、余文菲、刘叔晏均健在,分别居于浙江新安江、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济南(1982年迁回北京),然而,她们皆无法与他复续前缘。
依据中央相关文件的具体规定,得以安排陈伯达的一名子女负责照料其晚年的生活。
在陈伯达的众多子女中,他的幼子陈小弟,在陈伯达倒台后不久,年仅八九岁便遭受了无端的囚禁,长达三年的时光,这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1988年11月4日,笔者有幸拜访了陈小弟。他是一位典型的书生,身形消瘦,头发整洁,身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,整个人给人一种1960年代大学生的错觉。陈小弟的生活自理能力相当有限,住所显得有些杂乱无章。显然,由他来照料陈伯达,并非最恰当的选择。
陈伯达的独女陈岭梅,在陈伯达失势之后,依照当时相关部门的安排,迁往南方,于南京谋得一份新职。尽管她对父亲始终怀着深深的怀念之情,但鉴于两地相隔甚远,沟通颇为不便。
鉴于陈晓农与陈伯达间关系和睦,且身为中共党员,且居住地石家庄毗邻首都,公安部门便决定邀请陈晓农前来对他进行照料。
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。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,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。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,也生活得不错。如今出狱生活待遇仍然不错。他家有客厅、书房、他的卧室、儿子和儿媳的卧室、灶间、卫生间。
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,陈晓农,性情随和,待人诚挚。妻子小张,贤淑朴实。他们细心照料着陈伯达的生活。

周、陈、林集会
室内摆放着一张宽度超过一米的单人硬板床,床上铺着蓝白相间的方格床单,并配有一个大号的鸭绒枕头。床侧设有床头柜,两侧则是两个玻璃材质的书橱,窗边则放置了一个五斗橱。地面铺设了柔软的地毯。
我留意到一处细微之处:在寒冷的天气里,抽水马桶的座圈上,套着一个由毛线编织而成的护套。显而易见,这是出于对陈伯达年事已高、特别畏寒的考量;而陈伯达的枕头,不仅尺寸宏大,质地亦极为柔软,这无疑是为了让老人得以安心入眠。这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,实则彰显了儿子和儿媳对陈伯达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屋中时常迎来一位“常客”——那七岁的小孙子,正就读于小学二年级。这位小不点为家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温馨。
日复一日,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成了他固定的节目单。无论是播出的京剧或是古装故事片,他总是乐此不疲地观看。对于一般性的现代剧目,他则兴趣缺缺,然而,那些由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却能俘获他的心。至于那些讲述年轻人恋爱的电视剧,他则鲜少涉猎。
他热衷于阅读书籍与报纸。他常翻阅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以及《北京晚报》,对国内外形势的关注尤为细致。对于那些与“文革”相关的文章,他更是逐字逐句地研读。邻里间的情谊深厚,每当陈家无人外出取报时,邻居便会主动将报纸取回,挂在陈家门把手上。
他总要求儿子买书。
陈伯达,被誉为“万卷藏书家”。其个人藏书数量,早已超出了万册之数。往昔居住的四合院中,几间房间均被他的书籍所占据。陈伯达的薪水和稿酬收入,无一不投入到购书的行列中。陈伯达早年便开始赚取稿酬。然而,自1958年起,他主动提出放弃稿酬,将所得资金投入到国家建设中,自那时起,他未曾再领取过任何稿酬。
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后,每月领取一百元的生活津贴。据我所知,当时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亦如陈伯达一般,每月同样获得一百元的生活费。陈伯达每月的生活津贴中,三分之一被用来购买书籍。然而,这三十余元的购书资金对于陈伯达而言,显然是远远不足的。因此,他不得不借助老友之力,向相关部门借阅部分书籍。

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
自1983年2月份起,陈伯达的月生活费提升至两百元。自此,他购买书籍的经济压力得以缓解。与此同时,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的生活费亦同步增至每月两百元。陈伯达心中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归还他那些丰富的藏书。然而,相关部门的回复却一直拖延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,我发现陈伯达书橱中的书籍,大多是近几年出版的新作。
他对阅读的喜好涉猎广泛,尤其钟爱那些深具学术价值的著作。我随意浏览了他书架上的藏书,其中不乏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精装版、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》、《鲁迅杂文选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,以及曹聚仁的《我与我的世界》,谭嗣同的《文选注》、《红楼梦》诗词的注释本,还有《史记》等。此外,我注意到一本翻到一半的书籍,正是《圣经故事》。
陈晓农向笔者透露,在晚年,他的父亲陈伯达对文学名著情有独钟,曾多次叮嘱他专程购置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著作。
陈伯达彼时已届84岁高龄。即便居于宅中,他亦常年头戴一顶藏青呢质的干部帽,即便他并非秃顶之人。他的着装亦总是比我更为丰盛,身着铁灰色的中山装,搭配蓝色的鸭绒裤。他那眉角的眉毛尤其长,且视力、听力均保持得相当不错。他坐于沙发上,向我热情地打招呼。他事先便已得知我将进行采访,且亦研读过我的作品,对我也颇为了解。

陈伯达
我端坐于另一张沙发上,与他对面而坐,隔着茶几进行交谈。我提及:“陈老,早在1958年,我便有幸一睹您的风采。”
“嗯,1958年,那是在哪儿?”陈伯达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问。幸好,我能够理解他的话语。
“北京大学。”我回答。
谈及往昔,我回忆道:1958年5月4日,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,陈伯达莅临北大,于大膳厅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。彼时,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,有幸坐在台下聆听他那冗长的报告。他当时带来了一位‘翻译’,将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。这对我来说,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中国人向国人发表演讲时需要借助‘翻译’。这段经历至今仍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陈伯达大笑。
于是,原本略显尴尬的采访瞬间转化为轻松愉悦的氛围。
“列宁并不信任回忆录……”
我立刻回应道:“我并非旨在为你撰写回忆录,而是期待你能解答我的一些疑问。我已深入研读你的著作,并详查了你的专项资料,其中某些内容尚存疑惑。作为历史的亲历者,请随意分享,无论是多少内容,或是何种话题。我相信,你的言谈对我而言将极具价值。”

毛、林、周、陈
他沉吟片刻,未直接给出答案。转而向我发问,询问是否阅读过他有关孔子的论文。我意识到,这是他在对我进行考验。我立刻回应,确实阅读过,那篇论文是你抵达延安后创作的。主席(我知晓他习惯以“主席”称呼毛泽东)在阅读后,曾为你撰写了三封信件,其中两封是由张闻天代为转交的。
听闻此言,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,显然知晓我之前提及研究过他的作品并非虚言。我趁热打铁,询问他:“您是如何成为主席的秘书的呢?”
这一提问,是我事前精心策划的——在采访的领域里,这被称作“切入点”。选择切入点,务必精确无误。我挑选了一个既让他乐意作答,又能够充分阐述的问题作为切入点。若是以“如何与林彪勾结”这类问题发问,那无疑是自讨没趣。
的确,他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津津乐道地讲述了他是如何踏入延安的,又是如何初次遇见主席,以及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如何发言,进而引起主席的关注,那天主席又是如何特意留他共进晚餐……
“咱们不妨随意聊聊,无需录音。”

陈伯达与林彪
我唯有遵从。我深知,此刻不宜过于坚持——尽管录音在采访和资料保存方面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他与我闲谈之际,我主动询问了他笔名“陈达”的由来,以及“周金”“梅庄”“史达”等其他笔名的出处。他对此显得十分乐意分享。他深知,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些问题,显然是因为我对历史有着深厚的了解,并且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后才前来拜访他的。尽管这些笔名在档案中均有记载,却鲜有关于它们背后的故事。
在我看来,他的这些随意交谈内容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。我询问他的真名是否为“陈尚友”,他却予以否定。他解释称“尚友”是他的字,而本名是“陈建相”。接着,他详细讲述了关于自己哥哥、父母、家族背景、故乡福建惠安以及个人童年的往事,这些都是档案中描述不够详尽的细节。
我认为,不进行录音无疑是一大遗憾,因为笔录往往无法捕捉到所有宝贵的信息。我多次向陈伯达阐明,鉴于工作的实际需求,录音似乎更为适宜。我向他承诺,这些录音仅用于我的工作之需,绝不会被泄露。最终,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我取出录音设备,将其置于他面前,开始进行录音。
然而,随后的对话中,每当触及一些微妙的话题,他总会提醒我:“暂停录音。”我自是遵从他的指示。他简短阐述一番后,又会说:“现在可以继续录制了。”我随即按下录音机上的“播放”键。我对他的观点表示深深的尊重,而他也就更愿意与我畅谈。
于是,我的采访过程变得顺畅,尴尬之感不复存在。

陈伯达集会发言
“那就随意拍几张吧。”他并未明确回应,但那默许的神情似乎已不言而喻。于是,我拿起相机,开始了拍摄。而他,只是木然地坐着,面无表情。拍摄了几张后,他终于开口:“可以了!”我随即遵从他的意愿,停止了拍摄。
自那以后,我多次对他进行了采访。在对话的过程中,我们彼此之间逐渐拉近了距离。尽管如此,我始终保持着谨慎,最初只是谈论一些较为遥远的话题,都是他乐意分享的内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才逐渐触及了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,特别是那些关于“文革”的往事。
他的精神状态颇佳。偶尔,我们俩可以畅谈长达四小时,彼此都毫无倦意。
他变得愈发风趣。记有一次,我与他道别之际,他忽然叫住了我,提及有两点需要补充。我停下脚步,他却一时之间竟想不起具体是哪两点。那不过是短短几秒钟前的事情,他却已忘却!最终,他只得说道:“你明日一早再来,我再告诉你详情。”
然而,翌日清晨,我抵达他的住所,却惊讶地发现,他竟然连昨日提及的关于稍作补充的事情也遗忘得一干二净,坚称自己未曾提及任何补充。然而,当他回忆起过往,尤其是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往事时,他的记忆画面显得格外清晰,甚至对于当年郁达夫对其诗作所修改的几个字,也能记忆犹新,历历在目。

陈伯达与江青
他委托我返回上海,协助他寻找他一生中唯一一篇发表的小说,我成功找到了。在那日,我将复印本带至他的面前,为他朗读。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。那篇小说唤起了他诸多往事,他兴奋地与我分享着那些回忆。
我邂逅了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所著的回忆录,其中不乏对陈伯达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经历的生动描述。我将这些篇章朗读给他聆听。他聚精会神地听讲,并在过程中不时插言,追溯起那些昔日的场景。
“您能否把帽子取下?”出乎意料地,他竟然首次脱帽,让我为其拍照,甚至拿起报纸,摆好姿势,等待我拍摄。
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天,恰逢中秋佳节。那日,陈伯达显得格外愉悦,我捕捉到了他开怀大笑的瞬间。他更以毛笔挥毫,在宣纸上题赠了我一首诗。未曾想,这竟成为了他一生的绝唱。
七天后的1989年9月20日,陈达,时年85岁,于午餐时分不幸突发心肌梗死,终告离世。
庆幸的是,在陈伯达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——自刑满至终,我有幸作为唯一一位采访者,多次对他进行了深入访谈……
富灯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提升整个团队的作战能力
- 下一篇:没有了